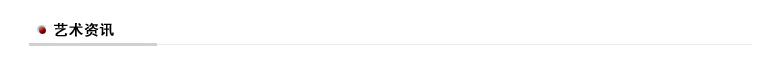|
在艺术展览越来越多、艺术市场越来越繁荣的今天,人们的一个直观感觉却是如今的展览有些千篇一律,令人乏味。一个展览的目的是什么?想说明或提出什么问题?学术主题或者文化针对性在哪里?选择艺术家的逻辑何在?这些需要被认真对待和慎重呈现的部分往往掩盖在了花团锦簇名流云集的开幕式之下。一个展览如何成立?它承载什么,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呈现,成为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于策展的讨论
本周在广州开幕的两个当代艺术展--风眠艺术空间的“to be or not to be”和南岸至尚美术馆的“与艺术上床”,是两个能让人记住的展览。
如今展览的数量并不算太少,仅以艺术生态活跃度远不及京沪等地的广州来说,每周也有十个左右的展览开幕,但是能让人长久记住并产生触动与思考的,实在却也不算太多。
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雷同的程式--十几位艺术家的名单毫无逻辑地堆在一起,一篇布满大词的前言高悬在展厅前方,这些艺术家中的一位、或者展场所在艺术机构的负责人作为策展人或者学术主持,但不论是从策展理念还是如何进入展览所选择的作品,你都休想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帮助。
展览空间与作品、作品与作品之间通常并不发生关系--如果不是互相干扰的话--那些画就只是简单地依次悬挂在墙上,与其说是“布展”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画廊式的陈列,有时墙面的颜色还喧宾夺主地鲜艳;架上雕塑甚至一件接着一件放置在展台上、展柜里,不可避免地分散着观看者的注意力。
某些作品像是“展览常青树”,反复地出现在各种“当代青年艺术联展”中,而这些展览却被冠以不同的名头与主题;与之相反而又相似的是,展览画册里一些所谓的评论文章,替换掉其中作品与画家的名字之后也完全成立。当然,优秀的作品仍然会让你印象深刻,但那是作品本身的光辉,而非策展的有效。
当下中国策展方式,随着策展人制度的确立越来越引起关注。去年11月,当今国际最活跃的策展人之一小汉斯在中央美院美术馆举行了题为“走向21世纪的策展”的演讲,以及跟中国策展人的即兴对话,探讨“策展面临的挑战”、“策展人与美术馆的关系”等问题。今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第二届CAFAM双年展,将主题定为“无形的手:策展作为立场”。由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联合主办的“亚洲美术策展人论坛”也将目光投向了“亚洲”与“策展”。
策展是一个问题
那么,策展从何时起成为一个问题?
策展成为一个问题,大约始于“独立策展人之父”哈罗德·塞曼1969年策展的“当态度变成形式”,那次展览首次在欧洲推出博伊斯、塞拉等改变了当代艺术思维的艺术家,也显示出了独立策展的价值。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西方的独立策展人制度开始进入中国香港及台湾地区。
1989年,由高名潞等批评家在中国美术馆策划组织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策展史的开端。之后1992年“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也同样由批评家所主导,虽然当时“策展人”这个概念还没有被使用,但是批评家们承担起了策展责任,对展览的学术方向进行了把握。
与美协等官方机构举办的巡礼、检阅式的群展不同,批评家们所主导的独立策展一开始就体现出从学术讨论到实践操作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每一个展览都试图提出或解决某个问题。这种提问并非对参展作品的生搬硬套,更不是给出主题之后要求艺术家们“命题作文”,而是基于策展人、批评家对艺术史、艺术当前问题的长期观察与深刻思考提出的。正因为这样,从这些展览以及2000年以后众多高质量的展览中,观看者可以梳理出一条脉络清晰的当代中国艺术发展路线。
近十年来,当代艺术策展又体现出媒介细分、文献并重、强调互动的趋势。
简单地说,媒介细分就是独立影像有独立影像的专门展、新媒体艺术有针对新媒体艺术的展、行为艺术有行为艺术节、独立动画有独立动画的展览……各种最新出现的艺术媒介都获得了更专业的关注与研究,这对艺术家、研究者、观众、潜在收藏者来说都是好事。
而文献并重,也不是像过去那样简单地罗列一下艺术家生平履历和曾出版过的画册,而是更有机地填充展览内容,诸如手稿、日志、通信、出版物、图片、视频……帮助观看者理解展览的美术史逻辑。强调互动就不用解释了,当代艺术展览们试图使用各种方式与观众互动,让观众参与。
可是,在策展方式逐渐固化、成为套路的时候,它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了。策展改变了“挂画”的过去,却又陷入一个彼此相似的现在。
传统策展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青年策展人崔灿灿认为,传统策展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现在的语境变得复杂而破碎,交流也越发快速、短暂、带有各种个体的成见,因此,再沿用上世纪90年代的策展方式来面对今天的问题,就很困难。
策展人唐佩贤也这样想。英国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博士唐佩贤是第一位华人策展女博士,她研究的课题《中国行为艺术发展1979~2010》对国内行为艺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今年9月,她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际行为艺术研究中心。11月8日下午,她策划的“to be or not to be”展在二沙岛风眠艺术空间开幕,与四位女性艺术家白蕾、孙少坤、汪华、朱利页共同用艺术的方式探讨人类的潜意识与梦境。
关于这个展览,风眠艺术空间总监姚远东方早在大半年前就已经满含兴奋地对我说,这将是一次“大胆的、令人大吃一惊的”尝试。的确,为了这个展览,整个空间的结构都做出了改变。
原有的影壁墙体被拆除、移动、隔离成四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大量泥土被搬上二楼用以种植芦苇……布展期间,甚至空间所在大厦的管理人员都跑来问问他们是不是要装修。在开幕式那天,许多风眠空间的老朋友一进来就吓了一跳。
无独有偶,11月11日晚间在南岸至尚美术馆开幕的“与艺术上床--广东当代中青年艺术展”也在展厅空间里做文章。原本空旷规整的展厅,被分割成六间不同色调的“样板房”,六位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分别占据一间,而每间“样板房”中最醒目的却是各具特色的一张大床。每个单独的空间都体现着艺术家独特的个性,也迎合着作品的风格,但整体看来,又是沿着“从晚上九点到早上七点的时间段”的顺序,提示着从“将寐”、“沉梦”到“眠觉”的过程中,人在私密空间中与床的关系。
在空间改造方面,民营美术馆具有天然的灵活性。只要馆长或者说投资者首肯,为了一次展览对场馆建筑本身进行改造,是可行的。广州53美术馆就曾经为举办“广州·现场”国际行为艺术节和“8+8当代国际影像展”而不止一次地改造过展厅空间。53美术馆馆长、《画廊》执行总编李琼波曾经告诉我,一次策展人拿着艺术家的方案来问他,说可能会对展厅地面造成破坏,是否可以接受?他回答说:“给艺术家最大的自由,宁可把地板砸了,也别逼着人家改方案”。
另一个例子是逵园。2012年初,黄轶群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位于东山口的逵园艺术馆。这个依托于恤孤路9号这座建立于1922年的东山名园而设的艺术空间,因为是文物保护单位而无法在空间结构上做太多变动,但总是根据展览的不同进行微调。逵园策划的,往往不是大规模展览,而是适应性更强的一些展览,强调作品本身的价值,也吸引到很多艺术家与参观者。
而公立美术馆则往往受限于各种原因,无法对每一个展览做出针对性的调整。
建成于1991年的岭南画派纪念馆是一座收藏和陈列岭南画派作品的专门机构,因此在设计之初是按照博物馆的陈列方式,绕墙一圈都是玻璃隔离的恒温展柜,而当它被用来承载当代艺术的策展时,这样的空间就显得有些限制性了。
今年10月在这里策划“以梦为马--青年艺术家16面体”群展的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车建全教授告诉我,这一点儿也不能改变的展示空间和传统博物馆形制的展柜让他大伤脑筋,最后只好把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挂在展柜里面,外面在玻璃上用马克笔涂鸦的形式注明创作理念之类的东西,“让手写而易逝的文献与略被遮挡又不影响观看完整性的作品形成空间上的透视与呼应,算是稍微给展览呈现带来一点变化。”
策展,不在于脱离主旨的撒野
当然,并不是说好的策展就一定要大动土木,也不是说改变展览空间就能让展览成功,前文所述的两个展览,好就好在它们空间的变化与展览的主题是契合的、是必要的,而非脱离主旨各自撒野。
在“to be or not to be”里,讨论的是意识与潜意识并存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
唐佩贤说,弗洛伊德提出人类的精神层次包括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而潜意识又代表着人类更深层、更隐秘、更原始、更根本的心理能量,包括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To Be Or Not To Be “展览主题正是从人类的潜意识出发,探讨艺术家如何将自我潜意识中的遐想,欲望及梦境用装置,绘画,影像,行为的方式还原。”当被受压制的部分无法抒发的时候它便开始寻找另一种观念途径去将其物化,那么我们可否通过艺术家将潜意识中不能成为意识的部分用艺术作品将之转换物化,通过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将现实生活中无法用实质表达的观念通过艺术的途径表达体现出来?“
对于这一问题,四位艺术家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回答。
艺术家朱利页借助催眠的方式寻根,她告诉我,她并没有经历过中国画的训练,但她认为文化的根源不是笔墨图示的回归,而是民族心理原初的探寻。
为此,她选择自我催眠,让意识淡化,民族集体无意识浮现,并在这种状态下创作。她发现在催眠的不同层次,画面的可辨识程度也不同:催眠较浅时,画面中还留有中国山水画或折枝花卉的影子,随着催眠的深入,她解读画面中呈现的是”华夏民族发生初期的平原记忆与亲水记忆,这与西方文化的磊岩记忆完全不同“。
艺术家孙少坤将芦苇、苍耳、枯井、棺材这些道具带入属于她的空间,叙说性与暴力,在其中演绎一场”野有蔓草“的行为艺术。
白蕾的影像装置发生在高达三米的白裙子里,想象人在潜意识支配下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观看者随时可以写下他们的感受,不论是”失控“、是”恶心“、是”我在“、或是”接受“。
汪华的”线团“串联现实、幻象与梦境,而这所有的作品得以成立,都是依托于空间改造之后恰到好处的支持。
唐佩贤说,展览策划时间长达一年,对室内空间的改造也经过了反复推敲,”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配合艺术与潜意识这样一个主题,希望观众可以与作品之间产生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掠过。“
“与艺术上床”的空间改造也同样与展览主题息息相关。
展厅中六个相互独立又相互通联的“样板房”让作品呈现得合理,竖起放置在门口任观者拍照留念--并且忍不住想找点油漆泼上去--的大床,让人想起罗伯特·劳森伯格那件著名的《床》,并由此展开“美术史与床”的畅想。
展览采用六位评论家或博士与六位艺术家一一对应,“在床上深入对话”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在私密、自由、放松的状态下打开自己。
展览的参与者之一、艺术评论家胡斌告诉我,这样的空间构成有众多的优点:“第一,这样类似家居空间的布展方式,让观者可以直观地想到这些艺术品回归生活空间之后主体的呈现,让人们更容易亲近和理解它们;第二,这种对私密空间的模仿,让艺术品从殿堂进入生活,消弭了观者与艺术品之间的界限,取消传播中的隔绝感;第三,批评家和艺术家的对话方式发生了变化,一般我们与艺术家是用一种学术定位的方式去对话,但是实际上艺术的对话往往在自由随性的环境下能进行得更好,在床上,或者用另一种说法,让人可以绝对放松的私密空间里,做艺术对话,对我来说也是特别的体验。”
策展需要无惧非议
如果说“to be or not to be”的开幕式像一次整体性的行为艺术,让参观者感到震动与不安,那么“与艺术上床”的开幕式则更像一场秀。
结合了歌舞表演、艺术家写真(六位或帅气或美丽的艺术家本人的写真照甚至多过他们作品的镜头!)、主题微电影拍摄与播放、台上两两相对的脱口秀以及台下床吧一般的嘉宾坐席、身穿小熊睡衣的服务生以及永不缺席的红酒……看起来很有些喧宾夺主。我身边的观众说,整晚两个小时的节目看完,都没搞明白每个画家是画什么的。
对于各种质疑,南岸至尚美术馆的馆长许多思表示早有心理准备:“我知道对于这次展览的开幕秀,大家会有很多争议,可我却一直是个无惧非议的人,在我眼里,坚定信念的自HIGH远比别人的认同来得重要。我们想尝试各种可能性--艺术的可能性、策展方式的可能性。”
今年7月,画家宋洋策划的798展览“魏毅个展及‘与艺术上床’行为摄影活动”在微信圈被爱艺客微信传播之后,引起人们的不少欢笑。宋洋用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西方美术史上那些与床有关的重要作品,而南岸至尚的“与艺术上床”,在文献梳理工作上超过宋洋所做的工作。
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美术学系副主任、《美术学研究》执行主编丁亚雷也是参与这次展览的六位评论家之一。
他解释说,床的概念在艺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一段关于“三张床”的对话,他用“理念形态的完美的床、我们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床、艺术家参照真实的床所画出来的床”的比喻,来告诉人们如何理解“理念的真实、现实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并认为艺术的真实不过是对理念至高之美的模仿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
在现代艺术史中,这“三张床”的概念被一位叫克罗斯的艺术家置换成了椅子,为人们提供了艺术品、艺术品背后的文本、观念以及生成的图像的并置,以及关于实物如何成为艺术、观念如何成为艺术的思考的启发。丁亚雷说:“(这个展览的概念)不仅仅局限在我们平常睡的床,而是通过这个实体的床让我们上溯到艺术史最早的一个阶段,并对艺术产生思考和定义,我觉得很有意思。”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方旭东在丁亚雷的提示基础上做了更多的工作。
他们梳理了从中国古代床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与其在美术作品中的表现,到西方自伊特鲁里亚文明壁画到文艺复兴以及现代主义、当代艺术中床这一元素的不同呈现;采访了36位广东艺术家,倾听他们与床有关的创作、思考与喜好;收集了六对批评家与艺术家全然开放的对话记录以及所撰写的文章,还有时尚杂志一般的艺术家写真。在此基础上,编撰成了一本厚达2厘米的……艺术与时尚画册。
没错,南岸至尚最初策划这本画册时就想摆脱常见的展览画册、文献模式,参照时尚杂志的定位设计。好的策展,除了现场的呈现之外,引发持续性的思考与相关学术整理与出版也是必要因素,仅以出版而言,不能简单地评价南岸至尚的尝试是否正确,但至少是一种饶有新意的试验。

孙少坤行为

汪华作品汪华作品

白蕾影像装置现场 |